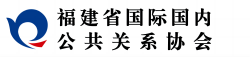前不久,来到当年安排上山下乡知青1.8万多名为福建全省之冠的县级建瓯市,参观了位于小松镇穆墩村的知青博物馆,看到李庆霖1972年12月20日写给毛主席信的手迹。这封信勾起一代人的回忆,也使我不禁想起多次采访李庆霖的往事。
一、熟人老记神秘兮兮地找上门
李庆霖斗胆上书毛主席“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等问题后,1973年4月26日毛主席亲自给李庆霖复信。
4月28日上午8点半,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到我当时工作的莆田地区革委会宣传部通联站,即福建日报通讯员联络站,有点神秘兮兮地找我。
赖玉章时年40出头,是位老记者,广东梅县人。此前通联站站负责人江维芳跟新华社福建分社林麟社长联系,派我这个新闻战线的新兵到福建分社见习记者采编工作,由赖玉章培训我。
我到分社招待所住下,由老赖带我到当时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单位闽侯县祥谦公社杨厝大队和地瓜乡惠安县山腰公社下坑内生产队采访,指导我写初稿并指点修改,稿件由总社发通稿并由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先后刊登。
于是,这次赖玉章便来找我这个熟人了。这天上午,通联站负责人江维芳也在办公室。老赖说找小魏出去聊聊,并没说采访的事。出去后,老赖说要我一起去采访一个人。他拿出一张手写地址的纸条给我看,我说这地方我知道,就在我地区机关院子后门凤山街居仁巷 。
我带老赖走到小巷一个叫“尼姑庵”的机关文工团宿舍斜对面小胡同居仁巷,找到一座一层平房,对上门牌15号,走进大门,只见右侧一块小空地上围一个简易羊栏,一只约莫10来公斤的大山羊对我们探头探脑。
二、电报把聊补错写为“贴”补
走入厅堂,李庆霖闻声从右侧卧室走出来,不冷不热地招呼我们。
坐下后,赖玉章报了二人身份,郑重告知:“李庆霖同志,毛主席给你回信了。”这时我才知道赖玉章的来意。
老赖取出一张明传电报,带着浓重的广东乡音宣读:“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贴’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听了,兴奋得直搓双手,不知所措,一时说不出话来。突然,他大声叫出老母亲和妻子出来跟我们见面,说毛主席回信啦!他一再表示“感谢毛主席,感谢记者到访”。
接着,李庆霖答记者问,说他在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当语文教师,工资较低,妻子张秀珍没有工作,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不能自食其力,次子李良雄和女儿李良陪在家吃闲饭,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所以才写信给毛主席。
赖玉章问,信是怎么寄给毛主席的?
李庆霖答:是写北京外交部王海容先生收,里面附一封信请王海容先看看由她决定是否转呈毛主席。
我注意到厅堂一角有一张竹方桌。李庆霖说,信就是在这张竹桌上写的。信发出后好几天惴惴不安,担心信会不会被截留。
如果信封上直接写毛主席收,怎么能收到啊?他说信是从离他家较远的莆田外环路丁字街口百货商店门外街边绿邮筒投入的。
随后,李庆霖按照老赖提示,正式回答了他对毛主席给他回信的感受和意义。因为当时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没有正式公开并宣传,赖玉章这次是作为内参稿件写了发到北京新华社总社。
当时新华社发到福建分社的明传电报写错一个字,把“聊”补无米之炊写作“‘贴’补无米之炊”,以致赖玉章给李庆霖宣读毛主席回信,以及随后他去找莆田地区革委会主任韩依民、副主任许集美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时,也都说成“‘贴’补无米之炊”。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亲笔复信。他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见信是用毛笔横写繁体字的。
到了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后,我才知道信中那句是“聊补无米之炊”,而非“贴补”。
在莆田县体育场召开庆祝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群众大会上,许集美在念完毛主席复信后还点评说,毛主席真伟大真谦逊!百忙之中还给一个平民百姓、普通教员回信,还写“寄上”,而不写“寄出”、“寄去”,多客气啊!寄三百元够多了,还说只是“聊补”。还写“容当统筹解决”,这“容当”一词用得好,多谦虚多客气啊!
三、赶快买张毛主席像贴上
这次我陪同赖玉章到李庆霖家采访,注意到他家15平米左右的厅堂没有窗口,阴暗,但没注意到厅堂是否安装电灯。过了一会儿,我们才适应昏暗的环境。
我环视厅堂墙壁,没有张贴毛主席像。当时,家里厅堂张贴毛主席像,有些人家还摆放毛主席石膏像,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是个普遍现象,甚至连地富反坏右分子家里都贴毛主席像。不然,会惹麻烦的。
我发现这一重大情况后,在采访结束将要起身告辞时,严肃地对李庆霖说:“毛主席给你回信还寄上三百元,这恩情和意义非同一般,可是你家你这厅堂怎么没贴毛主席像啊?赶紧去买一张贴上。”
赖玉章听我一说,环视四壁:“是啊,怎么没贴毛主席像,买一张花不了几块钱。”
李庆霖听了,直搓两手,连声说:“对,对,对!”
他送我们到门口,羊圈里的山羊见主人出来还“咩咩”叫几声。李庆霖说:“这羊是母的。养着挤奶给孩子增加点营养。”
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福建日报约稿要李庆霖谈谈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写几百字作为报纸综合新闻的一个事例,我第二次走进李庆霖家采访,便留心看看厅堂,正中间已经贴了毛主席画像,是用浆糊直接粘上的。我说:“贴上毛主席像,好啊!”
李庆霖笑笑,搓搓手。他有个习惯,感到突然、惊异、兴奋和不好意思时就搓搓手。
据说后来每看到毛主席像的新版本,李庆霖都会买一张,也不再是直接贴到墙壁上,而是放入镜框叠在旧像上挂在墙壁上。
四、“我平生喝过的最好茶叶”
我第二次去李庆霖家采访时,主动告诉他我办公室在地区机关食堂背后二层楼一层西头楼梯口斜对面,请他有空来坐坐。
暑假一天上午9点左右,李庆霖来办公室找我,刚好我在,赶紧迎上去,拉他坐在我身旁一个座位上。拿出我自用的白瓷杯,放上一小撮茶叶,泡上开水端到他面前。
我说,那天到你家采访,报纸只作为事例登了百来字,我拿出福建日报剪报,指点那几行文字给他看,他客气地站起来搓搓手,说:“谢谢!”
我示意他喝茶,他翻开杯盖,呷了一小口,赞叹:“好茶,好香!这是我平生喝过的最好茶叶!”
惭愧!这茶叶其实很差。当时我没有喝茶习惯,大学毕业一年转正工资为57.5元,汇款25元给父母,哪有闲钱买茶叶呀。
闽清报道组组长黄拨灼送我一包绿茶,久放宿舍,考虑到李庆霖可能会来找我,才从桌子边柜取出茶叶,打开闻闻,可惜变质了,霉味挺重,便拿到铁锅里微火炒炒,取出预先从机关院子里摘的7朵玉兰花拌入茶叶再装到罐里。昨天才拿到办公室,今天刚好让李庆霖喝上。
“我平生喝过的最好茶叶”,这也透视出李庆霖“无米之炊”的生活窘迫。
当时他工资只有42.5元,要养一家6口人,怎能享受茶叶啊!
五、“感觉你手提包里放手铐”
一来二往,李庆霖跟我算熟悉了。这次他来我办公室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刚好只我一人在办公室,交谈中他不再拘谨。
当时我还配挂一支驳壳枪,但我陪同赖玉章首次到李庆霖家并没带枪。这次李庆霖见枪,眼露惊异。我解释说,我除了给报社、电台写稿外,还跟随莆田地区革委会主任、6789炮兵部队师领导韩依民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 ,因他部队跟过来的小杨秘书患肝炎住院,便叫我替代,韩主任还给我一支手枪,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使用。他说到平潭、福清沿海一带为了安全,带枪为好。
李庆霖说:“那天你同新华社记者到我家,我第一个感觉你们是公安便衣。你手提包里放手铐呢!”
他说,给毛主席的信寄出去后,估摸着收到了,“随时准备公安局来人铐走我。”可见他随时准备应对写这信的政治风险。
我说,现在你可以放心啦!你反映的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引起毛主席高度重视和亲自回信,你办了大好事。全国知青和知青家长都会感谢你。
六、杜聿明没枪毙不等于伪保长不枪毙”
过一段时间,赖玉章又来莆田找我,说要到李庆霖任教单位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采访他。
我事先打电话通知莆田县报道组请转告城郊公社叫书记亲自出面接待新华社记者。但那时莆田不重视记者采访,基层干部甚至不懂得“新华社”是啥东东,还以为“新华社”似同“城郊公社”级别的单位。
我跟赖玉章一人坐一辆“自行车背”到了城郊公社门口,我付了每车3角共6角钱车费。到里面办公室,不见书记,有人告知书记下村去了。由公社秘书带我们到下林小学。
采访是在一间教室里隔着课桌相坐而谈。这次,李庆霖放开谈。我们得知他1936年出生,1952年当过莆田县一个中学校长,因为敢提意见,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贬到下林村小学任教。他1958年大跃进时因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
从当时的时势观点来看,李庆霖给人的印象是思维敏捷,看问题深刻,说话朴实幽默,有些话还相当尖锐。
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主席“告御状”,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并亲自回信,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调整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解决知青生活和回城工作出路等问题,以及对迫害知青特别是强奸女知青的基层干部严厉整治的一个契机和抓手。
那段时间,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以及福建日报,频频约稿,特别是每次重大政治运动与活动和每次“最高指示”发布,新华社福建分社和福建日报社一般都会来电通知我单位并基本由我出动采访李庆霖,收集李庆霖的心得体会,但稿件只写一两百字作为事例电话传稿后被摘编到综合新闻见报。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叫他直说无妨。
庆霖当时提了两点要求: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二是他妻子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算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要求恢复工作。韩先楚都答应了,也很快落实了。
不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记者先后前来找李庆霖采访。一天晚饭后,李庆霖到机关礼堂看电影时碰上,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了他的文章《谈反潮流》。
从此李庆霖被称誉为全国反潮流英雄之一。莆田街头出现了“向反潮流英雄李庆霖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等大幅标语。他给毛主席的信还被编入小学课本。
李庆霖出名后,从下林小学调到莆田城关实验小学。他身兼多职,先后担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和县知青办副主任,1974年担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李庆霖当“红”后,特别是当了全国人大常委后,他自以为算中央领导人之一,飘飘然起来,目空一切,忘乎所以。对待采访,只有北京来的记者,他放在眼里;而对地方记者,他不冷不热,爱理不理。
一次,莆田地区革委会常委集中在莆田地区招待所会议室开会研究春耕工作,李庆霖突然闯进会议室,边走边问:“你们开什么会啊?”我在场,他视而不见。
常委秘书长贾林赶紧小声宣布:休息一下。韩依民、许集美等领导赶紧起身迎接李庆霖,向他汇报会议内容,他正儿八经地听着。
那年月,省里有重要会议或活动都通知李庆霖参加,与会者一个突出感觉是,李庆霖变了,变得傲慢,有时说话口气很大。在会上批廖马林(省里主要领导廖志高和马兴元、林一心)以及莆田地区主要领导肖文玉等人的言论都无限上纲上线,有些话异常尖酸刻薄,令人听了如芒在心。
一次,李庆霖找莆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许集美提出说:“莆田县革委会主任许增贵(山西籍南下干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枪毙!”
许回答他:“全国最大的走资派都没处理,怎么能枪毙一个县的革委会主任?”
李说:“杜聿明没枪毙,不等于伪保长就不要枪毙啊?”
太狂妄了!许集美无言以对。
七、最伤心的是沥青涂黑双手
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卷入政治漩涡,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是他自己主动狂热表演的结果。
李庆霖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1日被正式宣布逮捕。街上的标语写他是“四人帮”在莆田的黑手和爪牙、莆田打砸抢的总后台等等。
说他是“四人帮黑手”,把他双手用沥青涂黑游街。
游街回来后,李庆霖双手沾满又黑又臭的沥青,用水很难冼掉。当时他的心情糟透了,传闻说李庆霖感到最伤心的是沥青涂黑手。
他最想不通和一直不服的是,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可是“四人帮”姚文元还只判有期徒刑20年。他承认自己说过错话,犯有严重错误,但他绝不承认“无期徒刑”如此重罪。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来给予平反,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八、恢复低调做人
李庆霖被隔离审查期间,他的老母亲到地区机关见到领导模样的人都下跪:“我儿子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还回信,没有大罪啊,求求你们放了他吧!”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专程去农场探望这位“知青之父”。
农场有关领导得知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来意,难以拒绝,破例让他们跟李庆霖会面。这些知青对李庆霖感恩戴德,由衷地感谢李庆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希望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86年来福建主政的项南同志,纠正“四人帮”问题的清查扩大化,一些被审查处理失当甚至被错误判刑的地方领导、机关干部和普通群众得到纠正和释放。
比如被指控跟李庆霖有牵连而受批斗和处理的“老革命”许集美,也得平反和恢复工作,后来享受副省级待遇。又如被判死缓的“李庆霖爪牙”莆田糖厂职工、厦门大学毕业的郭隆德,被无罪释放,恢复工作。
在这种情势下,1988年李庆霖被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隔离审查到农场服刑,他头尾失去自由共16年9个月。1994年8月他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李庆霖回来后,仍住在那座低矮破旧的小平房,厅堂上挂把老吊扇。约莫6平方米的卧室,摆一张木板床和一张老式台桌,上面堆满书籍。他衣着简朴,不苟言笑,恢复了出名前的低调做人。
多半时间,他都在小卧室里吟诗挥墨,晚上看看电视新闻和莆仙戏,偶尔也到街上散散步,街坊邻里熟人碰见这位形容瘦弱,两鬂斑白的老人,仍敬重地叫他“李老师”。老伴去世后,李庆霖常到女儿李良陪家小住。李良陪凭自己游泳成绩被招工到省体工队,退休后单位还照顾她在食堂做后勤工作。
李庆霖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与进步,不知他有何感想。传闻他初到劳改农场时,还写了幅对联:“想念毛主席,坚持大方向”。他那“大方向”是什么不得而知,或许还是“老一套”。但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作者魏章官,福建日报要闻采访部原主任,写于2020年4月8日,修改于2021年5月4日)